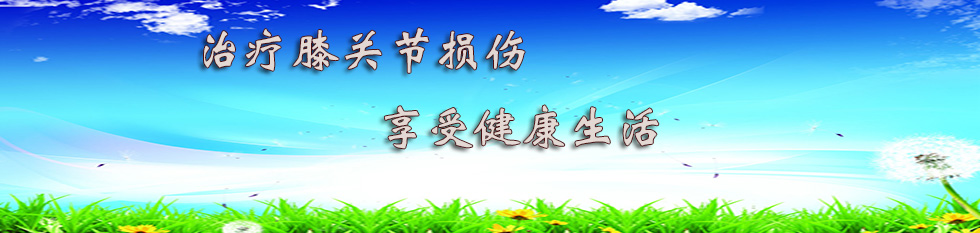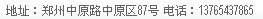|
缺铜会得白癜风吗 https://m-mip.39.net/man/mipso_7007739.html编译:丁鹏;点评:李永华 海军医院 美军在中东地区曾发起代号为“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OEF)”及“伊拉克自由行动(OIF)”的军事行动,期间产生大量伤员。本次带来RAPM杂志的一项研究,探讨伤后早期施行区域麻醉与伤病员报告的疼痛之间的关系。引言: 随着创伤比例及疼痛相关致残率的上升,创伤后的急性疼痛管理的改进成为决策者和临床医生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战地救护水平的进步使得战场生存率前所未有的提高,那些在OEF、OIF等行动中曾经面临死亡的伤员均得以存活。战伤患者中慢性疼痛比例超过80%,许多慢性疼痛伤员同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创伤性脑损伤(TBI)、抑郁以及机能减退。幸存者们需要持续、费用不菲的长期治疗、康复和疼痛管理。伤后早期阶段给予足够的急性疼痛管理可减少慢性疼痛,并由此增强康复效果。战场疼痛管理可减轻急性疼痛的强度以及心理后遗症的发生。RA可阻断传入性疼痛刺激,降低急性疼痛强度,并可能阻止中枢致敏和向慢性疼痛的进展。既往关于RA预防慢性疼痛的研究通常随访不到12个月,对象是术后平民人群,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战斗之初的大批量伤员流要求救治机构必须迅速具备救治能力。并非所有麻醉实施者在配属至战伤救治机构前均接受过RA培训。这种在武装冲突中实施RA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恰恰成为研究早期接受RA潜在获益的良机。本研究评估了OEF/OIF行动参战人员以及曾受肢体战伤的老兵的疼痛预后,主要指标为受伤后7天内接受早期RA(以持续周围神经阻滞(CPNB)为例)治疗的伤员,与未接受治疗的伤员相比,在受伤后24个月内平均疼痛强度会降低。次要指标为战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和心理症状等。方法: 研究设计此研究是一项针对参战人员战伤后是否接受早期RA的前瞻性、观察研究。招募并纳入了.10至.11间在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和圣安东尼奥军事医疗中心(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急诊住院及住院康复治疗的患者。研究人员采用电话随访方式收集患者的情况,由于该人群的特殊性,随访工作中付出极大努力。作战人员受伤后的救治流程为:1.伊拉克或医院;2.撤离至德医院;3.转运至州立军事医学中心(例如上文所提及的研究对象招募机构);4.从急救住院部门出院;5.转至医学中心住院;6.门诊康复;7.返回全美各地家庭。我们尽可能多的收集患者的数据,伤后6个月内每月均进行随访,之后每3个月随访一次直至第24个月。救治路径和机构的复杂性,以及前瞻性研究设计的自身性质,会导致在标准采集节点采集到的数据可能并不完整。区域麻醉肢体受伤伤员除了常规的全身多模式镇痛外,根据前线麻醉医师的业务能力选择在撤离或转运至救治机构后的7天内接受外周神经阻滞。RA的最佳时机是受伤即刻,但撤离环境下现实条件所限使得准确的麻醉实施时间难以获知。选择7天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大多数伤员在此时间内经伊拉克/医院的救护并转运至德医院进一步治疗。绝大多数伤员的持续外周神经阻滞是在战地手术室医院完成的,文中关于早期RA的定义,即指受伤后一周内所进行的处置。在OEF/OIF行动中,部署麻醉人员时并未考虑其是否曾接受过RA培训,因此对于任意伤员在接受RA上可能无明显差异。在疏散过程中只要有麻醉实施者在场就会对其进行RA,因而创造了一个合理、均衡的分组,以此对比伤员接受RA与否后的结局。在战场上,麻醉实施者根据自身经验以及伤员病情进行置管并使用药物。RA组和常规治疗组均接受了常规的阿片类药物为主的全身镇痛。伤员可获得各种常规的静脉注射止痛药及其他急性疼痛干预措施。一些人除了早期RA外,在后期的治疗过程中也接受过其他RA,主要是在伤口清创等需要镇痛的时候。研究群体样本选自OEF/OIF行动中转运至两所州立军事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伤员。初步统计显示半数伤员均为肢体损伤,因此需要住院治疗以及住院康复的伤员均有条件纳入研究,排除因头部创伤而严重认知障碍者、听力丧失者以及因双上肢受伤而截肢且无其他替代途径可完成调查者。护士在招募研究对象时对其进行认知功能测定。因程序性问题还排除了通过筛选但在签署知情同意前转运至别的救治机构的对象。所有知情同意并纳入的研究对象中,接受过RA且完成至少两次随访者进入下一步统计分析。RA实施情况、人口统计学资料、伤情特点、临床数据等收集自战创伤联合登记处(JointTheaterTraumaRegistry,JTTR)。研究对象的受伤机制、受伤部位、伤情评分(InjurySeverityScores,ISS)各不相同。其中ISS评分为0-75分,与死亡率和发病率相关。图1.研究流程图研究指标主要观测指标为平均疼痛强度,采用简明疼痛量表(BPI)进行测定。BPI量表采集最近一周内的平均疼痛强度、最痛强度以及最近一次疼痛强度,分值从0分(无疼痛)到10分(极其疼痛)。此外,受试者根据疼痛对其功能、活动、心情、行走、工作、人际关系、睡眠、生活乐趣等的影响进行评分,同样分数为0分(完全没有影响)至10分(完全影响)。对治疗缓解疼痛的程度也进行评分,从0%(不能缓解)至%(完全缓解)。为了多维度地衡量复杂疼痛,还采用了一些特殊的量表。神经病理疼痛10项评分表(NPS)可准确评估神经病理性疼痛并已在很多慢性疼痛人群中得到验证。该评分从0分(完全无感觉)至10分(最强烈),可分为疼痛强度和疼痛性质两个分量表,根据总的得分进行平均计算。疼痛治疗效果项评分表(TOPS)从14个方面采集患者的疼痛性质和治疗反应,评分从0分(疼痛不影响健康)至分(疼痛完全影响健康)。患者健康9项问卷(PHQ-9)可用于评估抑郁,此外还引入了简明机能39项评分(PCS)、精神健康评分(MCS)、创伤后应激障碍核查表(PCL)等量表工具。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记录伤员一般情况和伤情。采用单变量法分析治疗组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来检验平均疼痛和次级指标的纵向变化是否与早期RA治疗相关。虽然受试者在纳入时处于不同的康复阶段,各个受试者的数据收集月数也有所不同,但为了进行分析,所有个体的数据采集点都统一根据最初受伤到数据收集点的时间线性排列的。所有的模型都包括一个随机截距和斜率,以解释某个受试者观察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在检验疗效时将未接受早期RA的患者作为参考组。为了阐释初始受伤的严重程度,我们引入两个协变量作为潜在的干扰因子:ISS评分(即损伤严重程度)和在招募机构内的急救时间(如住院时间,以天为单位)。二者作为潜在的混杂因素以解释临床变异和可能对疼痛结局的影响。ISS作为损伤的直接测量指标,住院时间则作为损伤严重程度的次级测量指标。从RA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很难从各种生物和心理社会变化中单独区分出来,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疼痛相关的结果以及伤员的感受体验。我们假设RA可致获益,故在受伤后的前6个月和24个月期间检查平均疼痛和其他患者报告的疼痛相关指标。由于本研究基于假设生成的性质,次级指标和亚组分析都是探索性的,因此不适用于多因比较。如前所述,受试者是从美国大陆仅有的两个能够满足肢体战创伤患者急救需求的军事治疗中心的住院治疗或住院物理康复伤员中招募的。若受试者在初次受伤后的第一个月内被招募,则可从每个受试者上收集多达12次数据。然而,在重症监护期间收集这些指标其实很难实现。研究团队试图系统地招募所有在急诊住院治疗后符合条件的受试者,并对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进行控制如受试者的基线值和初始伤情。受试者可以在住院或康复的任何时间点进入研究,并在伤后的24个月内提供数据。因此,参与者的基线测量值各不相同。为了减少潜在的偏差,本分析中使用的模型以自受伤至今的时间为基础设计了一些估测指标,以便将所有数据点调整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线上来。我们分析了几个相互作用的因素以评估潜在的偏倚。我们根据受试者自初始受伤至进入研究之间的时间,将队列分为多个亚组。通过分析各亚组和RA之间的关联,来检验在不同阶段纳入研究是否会造成偏倚。结果显示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表明纳入研究的阶段不同不会引起系统性偏倚。我们尝试分析了治疗方法与受伤年份之间的关联,以观察随着区域麻醉的流行趋势是否会引起差异,结果显示治疗方法和受伤年份之间无显著关联,因此二者被排除在最终模型之外。基于以上阴性结果,间断缺失的数据可视作随机缺失。我们通过检验失访指标与治疗组之间关联的敏感性分析来评估失访者与完成研究者之间的治疗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并不显著。我们还根据研究中数据采集点的数量将队列分为亚组,检验随访持续时间和治疗效果之间的关联,评估不同的研究持续时长是否会给治疗效果带来偏倚,同样,结果并不显著。结果 研究流程图见图1。参与者资料最终的样本包括名参与者,其中人接受了早期RA,人没有。平均年龄为28±7.5岁,大多为白人男性。受试者平均接受6(±3)次随访,两组随访次数无统计学差异。统计中发现RA组与常规治疗组相比有以下差异(详见表1):受过大学教育的参战人员中接受早期RA的比例为25.4%vs.14.2%(p=0.);海军陆战队中接受早期RA的比例为11.1%vs.23.7%(p=0.);爆炸伤患者中接受早期RA的比例为82.5%vs.72.4%(p=0.);头部外伤患者中接受早期RA的比例为61.9%vs.50.9%(p=0.);上肢外伤患者中接受早期RA的比例为61.9%vs.51.1%(p=0.);因持续损伤导致截肢的伤员中的接受早期RA的比例为47.6%vs.31.0%(p=0.)。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经多变量分析发现,没有一项与最终结果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相关。随后进行二元检验表明,在建模中纳入ISS评分可以解释损伤类型的异质性。有研究表明,未完成高中教育/普通教育与健康水平低下之间存在关联。本研究中所有受试者都完成了高中教育/普通教育,将此变量纳入多因模型中未显示对结果有任何影响。两组患者的平均ISS无统计学差异,ISS和RA之间的相互关联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早期接受RA与否与伤情轻重无关。表1.人口统计学与受伤特点统计RA与平均疼痛强度总体来说,整个队列的疼痛评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根据住院时间和ISS评分调整后,早期接受RA和平均疼痛强度降低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在受伤后的前6个月,早期RA组的平均疼痛强度BPI评分估计降低了0.5分。根据时间、ISS和住院时长调整后的平均疼痛评分,早期RA组为2.5,常规治疗组为3.1。至第24个月时观察到两组间平均疼痛强度降低程度的差异缩小。在24个月期间内,两组逐月平均疼痛强度均明显降低,但早期RA组下降更为显著。图2.主要指标:BPI评分的变化表2.伤员报告的疼痛相关指标次级指标在受伤后的前6个月,接受早期RA治疗的患者疼痛缓解率增加了6.36%。这意味着有72.48%接受早期RA治疗的个体疼痛缓解,而未接受治疗的对象中,这一比例为66.12%。两组在6个月后疼痛缓解程度无明显变化,24个月时组间无统计学差异。根据住院时间和ISS进行调整后,两组患者的最强疼痛强度和疼痛影响评分在24个月内逐月下降,在最初的6个月内出现较大的月均差异。(详见表3)总的来说,在各个时间点,RA组的神经性疼痛强度和总体疼痛程度都更低。神经病理性疼痛强度估计在24个月内平均降低1分,神经病理性疼痛评分每个月都会有所改善。其他方面,RA组在各个时间点的恐惧回避症状、疼痛症状以及焦虑反应均更低。两组患者在伤后对疼痛治疗的满意度均较高,早期RA组的平均次级指标改善较对照组高,但此差异在损伤后24个月时无统计学意义。在研究期间,两组的心理健康结果没有显著变化。平均MCS得分高于一般美国人的平均心理健康得分5分。受试者PCS评分低于一般人群的平均身体健康水平。两组患者PCS评分在受伤后每月平均改善不到1分。两组患者的PHQ-9和PCL评分均无明显变化。表3.次级指标讨论: 研究中我们观察到RA组伤员受伤后前6个月的平均疼痛强度和疼痛缓解程度的明显改善,在严酷的战场环境中,伤后早期接受RA与改善疼痛长期预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在战场环境下和战后收集数据过程中的固有缺陷给研究带来一定可变性,但在受伤后的前6个月和24个月内,两组间的平均疼痛程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在RA组中也观察到最强疼痛强度和神经性疼痛强度的下降,尽管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总的来说,无论受伤程度如何,所有受试者报告的疼痛结局在总体上有所改善。我们的研究扩展了RA在急性疼痛治疗中的应用。对手术患者的荟萃分析表明,持续外周神经阻滞的术后镇痛效果优于一般阿片类镇痛。尽管多学科专家推荐CPNBs用于术后疼痛管理,但RA在创伤救治中应用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早前一项对名战伤军人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接受RA其术后7天疼痛强度降低1.5分。我们的纵向研究建立在先前的一些横断面研究和为期较短的观察性研究的基础上,设置了明确的参照组,证实RA与战伤后从疏散到紧急救护整个过程中的疼痛强度和疼痛缓解有关。尽管研究中的受试者的受伤机制各不相同,但其24个月时的平均疼痛评分与中、重度受伤的平民样本是相似的。这表明受伤后早期接受RA确实可带来治疗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组之间疼痛评分的差异更具意义。由于本研究的观察性质、随访时间以及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平民人群慢性疼痛的研究,后者往往随访时间更短,所以未采用常规临床试验所用的观测指标。未来研究的重点是评估RA对疼痛相关次级指标的影响。这项研究也是对肢体战创伤患者报告的疼痛相关指标的拓展和补充。既往很少有研究系统地收集战伤后24个月内的健康指标或疼痛情况的多样性。本研究测量了从最初损伤到恢复期间的一系列疼痛相关症状。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接受早期RA治疗的患者与未接受早期RA治疗的患者相比,其平均神经病理性疼痛性质和强度评分更低,对治疗结果的满意度更高。次级指标的改善体现了恢复和康复过程中有关医务人员努力,但也暴露了分析战地应用RA与多年后使用RA治疗复杂疼痛之间关联时的局限性。与针对平民群体的研究文献相一致,我们发现接受CPNB对HRQOL评分的影响不显著。PHQ-9和PCL评分低于常用的抑郁和PTSD筛查阈值,并保持稳定。然而,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试者的PCL分数达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标准,这一比率大大高于一般人群。除了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在前瞻性观察研究中很典型的局限。在其他疼痛指标上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受试者在随访之前并没有对自身症状和活动进行记录,因而产生潜在的内在变异性。随访因受试者在退役后在全国各地的分散而变得复杂。因此,并非所有参与者在各个时间点都能获得数据。尽管我们努力在多变量模型中控制观测研究中未测量的混杂因素,但仍然不尽如人意。例如,如前所述,因为退役或从救治机构转出,使得在各个时间点从全体受试者那里收集所有既定指标变得更加困难。从战争区域获得记录本身就很困难,如CPNB中使用的特定镇痛剂和阻滞持续时间。应当指出的是,在本研究的进行过程中,麻醉实施者进行区域麻醉的技术和能力都在迅速发展,麻醉住院医师培训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重视发展各种RA技术以满足疼痛患者的需求。本研究没有收集麻醉实施者的水平、培训背景等数据,也没有对其进行分层。随着时间推移,不管麻醉军医被部署至战地还是在国内,受试者最终都是要接受CPNB的。在此研究期间,基于疼痛管理和麻醉军医训练等方面取得的很多进展,目前的《关节创伤综合治疗实践指南》已要求尽可能因需随时在伤员疼痛管理中使用区域麻醉技术。受伤2年之后可能会新现诸多影响疼痛结果的变量,此观察性研究无法控制这么多变量。相反,本研究重点是关于评估早期救治措施,特别是将麻醉人员纳入战救编制后,早期在战现场为伤员提供CPNB。战场环境下获得有关数据极其困难,例如,有其他研究报道,在民用三级救治机构中,接受CPNB的创伤患者的平均留置导管注射时间为9天,我们的观察研究无法准确地获取平均留置导管时间,因为缺乏CPNB初次置管时间的记录。有证据显示使用RA可预防术后持续疼痛,而不是CPNB的持续时间。由于种种局限以及疼痛相关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太过复杂,不管考虑进多少变量还是潜在的未纳入混杂因素,都很难将特定干预措施对慢性疼痛的作用单独分离出来。一言概之,RA组患者报告的疼痛指标在伤后前6个月显著改善,并在24个月内保持稳定。这一发现支持我们的假设,即早期应用CPNB阻断外周疼痛刺激与伤后6个月平均疼痛强度的大幅度降低相关,并持续24个月。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受伤老兵而言,在伤后的前几个月若能实现疼痛强度的适度降低,可能带来终身收益。有必要进一步评估RA在平战时疼痛管理中的应用。应将区域麻醉纳入战伤救治规范,因为早期使用RA与整个康复和恢复过程中的疼痛方面收益密切相关。研究中我们观察到RA组伤员受伤后前6个月的平均疼痛强度和疼痛缓解程度的明显改善,在严酷的战场环境中,伤后早期接受RA与改善疼痛长期预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在战场环境下和战后收集数据过程中的固有缺陷给研究带来一定可变性,但在受伤后的前6个月和24个月内,两组间的平均疼痛程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在RA组中也观察到最强疼痛强度和神经性疼痛强度的下降,尽管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总的来说,无论受伤程度如何,所有受试者报告的疼痛结局在总体上有所改善。我们的研究扩展了RA在急性疼痛治疗中的应用。对手术患者的荟萃分析表明,持续外周神经阻滞的术后镇痛效果优于一般阿片类镇痛。尽管多学科专家推荐CPNBs用于术后疼痛管理,但RA在创伤救治中应用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早前一项对名战伤军人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接受RA其术后7天疼痛强度降低1.5分。我们的纵向研究建立在先前的一些横断面研究和为期较短的观察性研究的基础上,设置了明确的参照组,证实RA与战伤后从疏散到紧急救护整个过程中的疼痛强度和疼痛缓解有关。尽管研究中的受试者的受伤机制各不相同,但其24个月时的平均疼痛评分与中、重度受伤的平民样本是相似的。这表明受伤后早期接受RA确实可带来治疗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组之间疼痛评分的差异更具意义。由于本研究的观察性质、随访时间以及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平民人群慢性疼痛的研究,后者往往随访时间更短,所以未采用常规临床试验所用的观测指标。未来研究的重点是评估RA对疼痛相关次级指标的影响。这项研究也是对肢体战创伤患者报告的疼痛相关指标的拓展和补充。既往很少有研究系统地收集战伤后24个月内的健康指标或疼痛情况的多样性。本研究测量了从最初损伤到恢复期间的一系列疼痛相关症状。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接受早期RA治疗的患者与未接受早期RA治疗的患者相比,其平均神经病理性疼痛性质和强度评分更低,对治疗结果的满意度更高。次级指标的改善体现了恢复和康复过程中有关医务人员努力,但也暴露了分析战地应用RA与多年后使用RA治疗复杂疼痛之间关联时的局限性。与针对平民群体的研究文献相一致,我们发现接受CPNB对HRQOL评分的影响不显著。PHQ-9和PCL评分低于常用的抑郁和PTSD筛查阈值,并保持稳定。然而,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试者的PCL分数达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标准,这一比率大大高于一般人群。除了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在前瞻性观察研究中很典型的局限。在其他疼痛指标上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受试者在随访之前并没有对自身症状和活动进行记录,因而产生潜在的内在变异性。随访因受试者在退役后在全国各地的分散而变得复杂。因此,并非所有参与者在各个时间点都能获得数据。尽管我们努力在多变量模型中控制观测研究中未测量的混杂因素,但仍然不尽如人意。例如,如前所述,因为退役或从救治机构转出,使得在各个时间点从全体受试者那里收集所有既定指标变得更加困难。从战争区域获得记录本身就很困难,如CPNB中使用的特定镇痛剂和阻滞持续时间。应当指出的是,在本研究的进行过程中,麻醉实施者进行区域麻醉的技术和能力都在迅速发展,麻醉住院医师培训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重视发展各种RA技术以满足疼痛患者的需求。本研究没有收集麻醉实施者的水平、培训背景等数据,也没有对其进行分层。随着时间推移,不管麻醉军医被部署至战地还是在国内,受试者最终都是要接受CPNB的。在此研究期间,基于疼痛管理和麻醉军医训练等方面取得的很多进展,目前的《关节创伤综合治疗实践指南》已要求尽可能因需随时在伤员疼痛管理中使用区域麻醉技术。受伤2年之后可能会新现诸多影响疼痛结果的变量,此观察性研究无法控制这么多变量。相反,本研究重点是关于评估早期救治措施,特别是将麻醉人员纳入战救编制后,早期在战现场为伤员提供CPNB。战场环境下获得有关数据极其困难,例如,有其他研究报道,在民用三级救治机构中,接受CPNB的创伤患者的平均留置导管注射时间为9天,我们的观察研究无法准确地获取平均留置导管时间,因为缺乏CPNB初次置管时间的记录。有证据显示使用RA可预防术后持续疼痛,而不是CPNB的持续时间。由于种种局限以及疼痛相关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太过复杂,不管考虑进多少变量还是潜在的未纳入混杂因素,都很难将特定干预措施对慢性疼痛的作用单独分离出来。一言概之,RA组患者报告的疼痛指标在伤后前6个月显著改善,并在24个月内保持稳定。这一发现支持我们的假设,即早期应用CPNB阻断外周疼痛刺激与伤后6个月平均疼痛强度的大幅度降低相关,并持续24个月。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受伤老兵而言,在伤后的前几个月若能实现疼痛强度的适度降低,可能带来终身收益。有必要进一步评估RA在平战时疼痛管理中的应用。应将区域麻醉纳入战伤救治规范,因为早期使用RA与整个康复和恢复过程中的疼痛方面收益密切相关。骨麻征途的点评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OEF:.10.07-.12.28)和伊拉克自由行动(OIF:.03.19-.08.31)是近20年美军在亚洲的主要军事行动,在行动中受伤的美军士兵人数分别约为1人和人。肢体伤伤员主要是爆炸伤和枪战伤引起,疼痛剧烈,传统的吗啡注射针镇痛作用有限,为此美军将持续区域阻滞的应用扩展到了战场条件下的伤员的镇痛。本研究的对象为.10-.11间在美国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和圣安东尼奥军事医疗中心入院接受治疗康复的名在OEF/OIF军事行动中肢体受伤军人,并对其随访两年。发现肢体战创伤后早期(7天内)接受区域麻醉(regionalanesthesia,RA)会明显降低急性疼痛程度,改善慢性病理性疼痛评分,提高伤员镇痛满意度。区域阻滞在日常术后镇痛方面的研究颇多,但用于战场环境下伤员战创伤镇痛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见。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未来战时和平时创伤救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无论士兵还是平民在受伤后早期启动神经阻滞为主的镇痛干预会有利于伤员的早期康复和远期收益。虽然本文并未列出实施持续区域阻滞的部位和种类,但是考虑到被研究对象是上下肢伤员,我们推断可能是以臂丛、股神经、坐骨神经等常见阻滞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大约10年前美军就能将这些神经阻滞应用于前线战创伤救治,并且是持续阻滞,其麻醉军医的业务水平遥遥领先他国。随着超声设备的广泛使用,神经阻滞的范围不断扩大,新型阻滞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头颅、四肢、胸腹部位的战创伤镇痛均可满足,并且日趋精准。这就需要卫生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麻醉军医的培养,大力配备超声设备,积极进行相应的区域阻滞训练,提高战时我军战创伤镇痛水平。(编译:丁鹏;点评:李永华) 原始文献:GallagherRollinM,PolomanoRosemaryC,GiordanoNicholasAetal.Prospectivecohortstudyexaminingtheuseofregionalanesthesiaforearlypainmanagementafter
|